我回復姚大力批評我所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很快有了回應。姚文的題目是《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載2015年5月31日《上海書評》)。然而內容並不是談如何略蕪取精,如何為我所用,而是針對我對他的質疑,並時而爆出情緒性的激憤之詞。在網上還有他的學生為之叫好,說他的姚老師“抽”了我!姚大力更將我的文字隨心製造矛盾,誇大其詞,甚至曲解之餘,代我認錯,取得爭勝的滿足感。是誰在“深文周納、巧言羅織”啊!眾目可見,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說“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職,卻說是兼差。就此而言,無論他的正題或副題,都有點文不對題。
我與姚大力素昧平生,全無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對事不對人,所以對事我針鋒相對,不稍假借,然對其人仍尊之為“姚先生”,並“敬答”對我所編之書的批評,這就是所謂對事不對人。但是他毫不客氣,不僅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輕蔑。類此針對個人的態度,我並不在乎,也不怪他,誠如他所說“入墨者黑”,我也只好隨俗了。
質疑新清史最主要的問題是清帝國的性質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根本是假議題,沒有人“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說“全面”,豈非誇大其詞?我所編之書就是如他所說,很具體地指出新清史立論中“那些關鍵性的錯誤究竟是如何”,何來全面否定?老姚優為者,不過是把別人的說法推向極端,然後加以抨擊。一言以蔽之,我們質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問題,是有關清帝國性質的大問題。既然說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諱才是正道,何況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蕪雜”能忽略嗎?我的理解是“蕪雜”必須充分揭露後,證明是“蕪雜”,才能略之。否則容忍“蕪雜”,“菁英”安彰?更未免鄉願。
我說姚大力“未讀懂”新清史的主要論點,是很具體的,但他誇大成“不識字”,有何意義呢?就像他誇張地說,“全面否定”、“一幅整體坍塌的可笑圖景”、“一團向壁虛構的夢囈”、“一堆不具有任何積極的正面意義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編荒誕的形容詞,除了他之外,誰說過這些話呢?我已具體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漢化”說,認為是一錯誤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們的原文來作說明,但姚大力仍然視若無睹。很顯然,“漢化”與新清史所主張的“族群主權”有矛盾,所以他們並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漢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認為歐立德將“漢化”理解為“全盤漢化”,其用意由於“漢化”難以否定,故將之極端化來否定漢化,因“全盤漢化”就像“全盤西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認為即使是漢人,也難說“全盤漢化”。所以如果把“漢化”理解為“全盤漢化”,則無“漢化”矣!但姚大力卻將之誤讀為歐立德只不同意“全盤漢化”,還要自問他為何不可用“全盤漢化”?他當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將漢化解作“全盤漢化”,以便否認漢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勸姚不要再硬拗“全盤漢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聞,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盤漢化論”者,有這樣蠻幹的嗎?
姚大力說我單挑“漢化”,就是他不讀何炳棣原文的亂點鴛鴦譜,何文不僅指責而且抗議羅友枝單挑漢化。羅既然單挑漢化,何老先生當然以“捍衛漢化”回應,如果羅不抨擊漢化,何又何須“捍衛漢化”?無“的”哪有“矢”啊!可是姚大力仍然要批評何文只談第三條的漢化。姚大力似乎還是搞不清楚,新清史不是要對“漢化”作正面的反思,而是根本質疑“漢化”此一概念與用法,甚至指責“漢化”乃現代中國民族沙文主義的產品,但姚大力仍然認為,新清史的“漢化觀”沒有什麼不對。關於新清史的“漢化觀”,我在前文已經詳述,就請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大清帝國既然擁有內亞,具有內亞屬性,自不待言,誰會去否定內亞屬性?但姚大力卻“又驚又喜”地發現我承認了新清史的“內亞視角”。請問我個人以及所編的整本書,何來否認“內亞視角”的言詞?關鍵是否如新清史所說,清帝國擁有遼闊的內亞之後,就成為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甚至中國竟是內亞帝國的一部分?姚大力對此最關鍵的問題,卻推說由於篇幅所限,不予表態!(事實上,他浪費了不少筆墨大談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他難道看不見,新清史誇大內亞屬性之後,認為清帝國融合兩種傳統之後,是一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是新清史的論斷啊!姚大力卻對我大興問罪之師。他引用我的結論,不提我的論證,大罵“錯亂”。正因為此乃有關清帝國性質的大問題,所以我們提出“商榷”,以回應新清史,主要反駁清帝國是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之說,未料卻觸老姚之怒。
歐立德厚達五百八十頁的大書《滿洲風》(The Manchu Way,編者注:又譯為“滿洲之道”)以八旗與族群認同為主題,包含甚廣,絕非如姚文所說“繼續維持滿漢界別”。他是要以“滿洲風”來取代“中華風”(The Sinic Pax)的。然而“滿洲風”能取代“中華風”嗎?顯然不能!就拿八旗來說,乃滿洲最根本的制度,請問滿族入關之後,清帝推行的是傳統中華一人帝制,還是八王共同議政制?答案不是很明顯嗎?姚大力認為內亞的政治文化資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卻不說哪些政治文化資源,也不說“至關重要”到何地步?是否如新清史所說,重要到已不能再稱作中華帝國了?姚大力說,有理由把清與漢、唐、宋、明的“統治體制區別開來”。漢、唐、宋、明都是中華帝國,區別開來清帝國即非中華帝國了?那豈不就是清不是繼明,而是繼元。言下之意,豈非與中華民國只能繼明的說法相當一致。這種主張姚大力能接受嗎?沒想到他居然說,在汪榮祖的心目裏,“滿洲傳統根本就不屬於中華傳統”!他老兄代言錯了,須知這話是在新清史諸君的心目裏,不是在我的心目裏。他對“代言”一詞,似甚敏感;其實我毫無貶損之意。你覺得產品好,為之代言,應該是光榮的事啊!但“代言”絕不可不誠實。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滿族入主中原是要做中國的皇帝,國號曰清,建都北京,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毫無疑問在中原。清朝治理內亞的方式與中原不一樣,因地設施,無足為奇,因仍在中原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更何況地處內亞的新疆後來也成為中國的行省。何炳棣說清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非內亞,並沒有認為漢化是清帝國成功的唯一原因,他一共舉了五個原因,但他認為清帝國統治政策的核心仍然依賴傳統中國的政策。這話並沒有錯,但姚大力偏偏要將何先生定型為一“尺有所短”的“極端漢化主義者”!中原漢人與漢文化對大清帝國的貢獻,何先生已經講了許多,姚大力不妨多講一點內亞的政經文化資源對清帝國的貢獻,如果能證明內亞的資源大於中原,足可以“內亞帝國”代替“中華帝國”,則新清史諸君必樂見姚大力能青出於藍也。
眾所周知,清帝國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多民族政權,中華帝國從秦到清,一直是多民族互動的天下。所以甘德星證明康熙自稱中國皇帝,至關重要,然而姚大力卻說不重要。新清史認為滿洲人“打扮成漢人的統治者”;換言之,實際上並不是,只是“打扮成”。西方學者往往把非漢人統治的政權視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征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征服者的王朝,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外來政權”,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不是“奇談怪論”的“大翻案”嗎?我並沒有說錯啊!我曾一再“敬告”姚大力,洋人只認漢人是中國人,中國學問叫“漢學”,滿人、蒙人、藏人都不是Chinese,但老姚還是聽不懂。所以我說美國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國家,卻不知中國也是一多民族國家,然而姚大力居然莫名其妙地說我也不知道中國是一多民族國家,能夠這樣子亂說話嗎?滿洲族群像漢人一樣具有血統觀念,然經過長期的歷史經驗,最終成為“歷史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華民族,但滿人或漢人都不宜被稱作“歷史民族”。滿洲認同沒有消失又如何?我曾一再提到,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兩碼事。中國人的省籍認同也從來沒有消失過,不是嗎?
姚大力說:“汪榮祖主張若非漢化,即成外國的說法。”請問我在何處說過這句話?此猶如洋人所說“把你的話塞進我的嘴裏”(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將漢等同中國是西方人的主張與說法,所以他們雖然把中國歷史上非漢人政權寫入中國史,但視為“外來政權”或“征服王朝”。事實上,這些王朝無論五胡、遼金元清絕非外國,即使是少數民族政權,仍然是中國。姚大力提到呂思勉,原來是要借呂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國。呂先生那一輩學者于辛亥革命後仍具濃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忘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更不應套用外國名詞,把元代視為“殖民地時代”,因大元就是中國的國號,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要做中國的皇帝,忽必烈又稱元世祖,也是中國的廟號。姚大力是元史專家,應該知道得更多。他也應該知道,即使呂先生雖不恰當地把元朝視為“殖民地”,但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不是嗎?但他卻以我認為寫入中國史,就是把元朝視為中國,有違呂先生的本意。臺灣從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日本殖民地,蒙古人到中國成立元朝,日本人並未到臺灣成立和朝,兩相比較就知道,說元史是中國被殖民的歷史是不符事實的。然而臺灣五十年被殖民的歷史仍然要寫入臺灣史,不是嗎?美國殖民時代也是美國史的一部分啊!老姚未免少見多怪矣!他更借此大玩文字遊戲,莫名其妙說我“清朝若非全盤繼承漢家傳統,即失去代表中國之資格”。我在哪里說過這句話?我一再說過,所謂“全盤漢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假議題,我一再說過大清足有資格代表中國。認為清朝不代表中國的是新清史諸君啊!他居然還要反問我,“清朝到底還算中國嗎”? 此一大哉問,你應該去問新清史諸君啊!需要“錯亂”地問我嗎?
清、俄兩大帝國的性質根本有異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國不能與俄羅斯帝國相提並論,因看起來都是“早期現代帝國”,但貌同心異。姚大力不能理會,寫了一大段來反駁。他接受俄國晚至十九世紀末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說法,但同時又確定俄國是已奉行帝國主義的帝國。按十九世紀末的“新帝國主義”的特徵是向海外擴張奪取資源、市場與勞力。請問若非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新帝國主義”的出現嗎?無因能有果嗎?列寧所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有其洞見,西方學者也未嘗因人廢言。即使不是“最高階段”,也必須要有相當階段才可能發生。姚大力問我“是不是社會發展五階段的追隨者”?這話在我聽來相當意外,因我一直認為任何學說,只要具有批評的眼光,都可為我所用。學術不是幫派,談不上“追隨”。若具有批評的眼光,就不會將一偏之說視為“主流”或“定論”。如姚大力跟著有些西方人,將帝俄視為“專制的和集體的非歐洲帝國”,真不必人云亦云,何不獨立思考一下:帝俄不是歐洲國家,難道是亞洲國家?即使可稱“歐亞帝國”,重心還在歐洲吧!
說到“資本主義”(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資金牟利的經濟制度,無論製造業與服務業都是為了市場供需,最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沒有政府干預的私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但純粹的並不多,即使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生產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與“控制”。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從一些譯書中找些說法,在抽象的名詞裏打滾,作言不及義的解釋。姚大力要“把克利歐還給克利歐”,那就請克利歐出來說明具體的歷史事實,看看十八世紀的帝俄是不是已進入資本主義。
俄國的彼得大帝與清帝國康熙大帝同時,已開始全面歐化,將俄國帶入西歐世界。他在俄國薄弱的基礎上建立了大規模的重工業,大大發展了紡織輕工業,輸入各種新型的製造業,以及成長四倍的國際海上貿易。在1695年俄國只有十七家鐵工廠,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發展工商政策的目的,固然是要富國強兵,由政府主導,但至1725年烏拉地區(Urals)百分之二十的鐵產已由私營,而早在1716年,高品質的俄國鐵器已出現在倫敦市場。當彼得大帝駕崩時,俄國所出產的生鐵已經略微超過英國,二十五年之後遠遠超過英國。到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俄國已取代瑞典成為歐洲最大的鐵生產國。從1710到1725年間,不少國營工廠轉為私營,彼得大帝也以優惠條件鼓勵創辦私人企業與公司。其實他早在1699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開設各種不同項目的工商業公司,發展貿易與各類製造業,他也從大商人與製造業者那裏得到相當多的資金來發展工業與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國的國際貿易額在彼得大帝任內已成長了四倍,且在整個十八世紀持續不衰。所以俄國東進到內亞與東亞以及西伯利亞,主要也是為了追求資源與商利。請問十八世紀的俄國有輕重工業、有各種製造業、有私有資本、有國際貿易與市場經濟,以及有追尋龐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認已經進入資本主義呢?在歷史女神面前還需要引經據典來強辯嗎?姚大力相信俄國晚到十九世紀末尚非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太“冒失”了嗎?他想送給我“冒失”的帽子,還是還給他自己吧。
反觀十八世紀的大清帝國也在盛世,康熙大帝雖從耶穌會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訊息,對西學也發生興趣,但幾乎完全沒有反映到國家政策上來。康熙經營的仍然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到乾隆晚年英國派使臣馬戛爾尼(George McCartney)來華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絕,就是不願意放棄原有的體制,被西方人稱為“遲滯的帝國”(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入侵,李鴻章才驚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很明顯的,清、俄雖同為“早期現代帝國”,但一進取,另一守成,兩大帝國的性質根本有異。我說“貌同心異”,姚大力不能會意,只好再列舉一些眾所周知的史實,供他參考。
侵略性與防禦性的擴張是兩碼事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與防禦性的擴張,其實略觀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脅是一貫的。明朝無力進取,只能築邊牆,做最保守的全線防禦;清朝具有的長城以北以及內亞的優勢,才能做進取的防禦,建立滿蒙“旗盟制度”,目的是和平相處,分而治之,以策安全,與西方的殖民制度,乃兩碼事。康熙征討準噶爾蒙古,因噶爾丹破壞此一安全體系,入侵內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詳細的敍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斷康熙征討噶爾丹的動機。就拿姚大力提出來的“義利之辨”來說,西方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幾乎全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圖?多的是勞民傷財,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為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大清既然是為了北疆的安寧與安全,可稱為“義”。無論如何,清朝在內亞的建制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制度,吳啟訥在我所編書中已經詳述,不必再贅,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於擴張動機的善惡固然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未嘗沒有公正客觀的可能性,至少善惡有程度之別,我想姚大力也不至於認為大清的擴張與新帝國主義的擴張是一丘之貉。善惡也未嘗沒有一致性的判斷,像二戰前德國與日本的擴張,全世界幾乎沒有人會說是“善”的。我說美國人都知道美國的西進運動,濮培德當然知道,但他卻以雙重標準來指責清朝的西進。姚大力未看懂,卻指我說濮培德“不是美國人”!
姚大力顯然對後現代理論很感興趣,所以引福柯講“話語”(discourse),但貿然引用,言不及義,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干。我既不曾說新清史是“話語構建”,也不認為是言之成理的“理論”,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確想要指出的,其實是所謂“實證史學偏見”,他要重“理論”輕“考據”。他說“崇尚考據本來是對的,但光憑考據無法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這不是廢話一句嗎?考據原是做學問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憑考據當然無法重建史實;然而如無嚴謹的考證,重建的史實能不“地動山搖”嗎?
他又貿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話,不知上下文的讀者有點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無法掌握這位著名英國歷史哲學家的要旨。柯氏反對的“實證史學”是指將史學科學化或遵循自然法則的史學,如佈雷(John Bury)與韓貝爾(C. G. Hempel)等人的主張,因他認為歷史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他認為歷史不可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運心重演往事,並非全憑主觀空想,仍然需要文獻佐證。他在自傳裏說得尤其清楚,解決歷史問題必須要拋棄猜測,而須充分滿足證據所需。在此不宜多談柯林武德以免節外生枝,總之他對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實證史學仍有敬意,考據也絕非“歷史編撰學的消極遺產”。據我所知,韓儒林就自西歐漢學中師承蘭克的治學方法,專攻蒙元史,擅長以多種語文史料校訂互勘,對名物制度的考證,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與部落名。考據不能“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嗎?
在西方,“學門”與“紀律”(discipline)是同一個字,學術紀律要求極嚴。進入學門的研究生需先學習該學門的基本學術規範,講究寫書評、寫論文的方法與格式,連註腳的格式都必須按照規範,如有不按規範的書評或論文,是不會被接受的。所以我很驚訝有人會說,書評可以隨便寫。在西方教你如何寫論文、寫書評的小冊子可多著呢。姚大力要大家虛心向外國學習,何莫從入門的學術規範學起?我不相信中國大陸的高校是以“世間人法無定法,而後知非法法也”來教導學生的。
學術批評不是“打棒子”
我認為與學術相關的個人見聞應是有參考價值的難得訊息,但姚大力認為這些“瑣聞逸事”是八卦。若說“認識她”或“一夕談”是八卦,那麼“先師”、 “老友”云云是否也是八卦?我猶記與他先師一夕之談,是充滿敬意的。姚大力引他先師所說“歷史研究中自築營塹、關門稱大王的封閉意識,以為既然研究的是本國的歷史文化,即可以旁若無人”,明顯是反映他先師的時代。在那封閉的時代,當然是十分正確而令人起敬的。但經過三十餘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與港臺一樣膜拜西學之風大盛,是否有“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連研究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也不如人”的現象?儒林先生若見此現象,還會說“關門稱大王”嗎?作為韓教授的學生不自覺時間錯亂,居然說我“先捧後抑”,不僅錯解人意,而且還要杠上開花,加上“輕誣前賢”的罪名,還要牽扯到陳寅恪。在他心目中,“尺有所短”與“輕誣前賢”是同義詞嗎?
最不可思議的是,姚大力說“在他自己主編的書裏也沒有獲得多少人支持”;如果是這樣,他又何必批評我主編的書呢?批評我就好了。遺憾的是,他老兄既不知有水準的研討會本來就不是“一言堂”,更昧於我們來回討論、修改論文,編輯論文集的過程。我們既有不同意見,也有基本共識,像你姚大力當然不會跟“我們”一起開會、寫文章吧!請問老姚,如果主編不能對他所編之書負責,又有誰來負責?如有人對一本論文集提出不當的批評,如果主編不回應,算負責任嗎?他不瞭解這些情況也就罷了,居然在情急之下,口不擇言。用他的話說,“是什麼意思?”他出此下策,恐將貽笑儒林。我編的這本書出版後,歐洲著名出版社Brill主動來函要求授權出英文版。西方有人對這本書如此感興趣,就是因為有不同的見解和批評的力度,與姚大力的心態正好南轅北轍。姚文總覺得我們不應該去批評新清史,而應該虛心向他們學習,把批評他們當作“棒子打到新清史頭上去”,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打棒子”嗎?
政治正不正確也是姚大力提出的議題,我只是回復他,他便死纏誰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對待”。新清史重新詮釋清帝國的性質,強調“族群主權”以及大清是內亞帝國而非中國的朝代,不應該有所警惕嗎?當下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眾所周知,目的就是為了“圍堵”中國,不希望中國太強太大, 難道姚大力毫無感覺嗎?姚大力真的相信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圖與新清史理論完全無關嗎?他人在境內,應該對學術被政治利用更加敏感。然而他還要反問我:“那些當年和當下的敵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姚文理直氣壯地說:“我說針對新清史的批評往往含有指責其‘政治不正確’的強烈意味,這麼說到底錯了沒有呢?”錯了!我們不會“指責”他們政治不正確,因他們根本不在乎政治正確不正確,我們只批評他們的立論,對他們的論述被政客利用感到遺憾而已。強烈意味的政治語言倒出現在姚文的最後一大段,諸如“把這樣的爭論看作學術領域內的一場政治鬥爭、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甚至發展為一種空言詆斥、辭氣叫囂的惡劣文風,就可能帶來非常不好的後果,不但無益于社會的文化發展,而且對政治發展也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這些無限上綱的政治語言令我感到十分陌生與錯愕,怎麼會出現這種話語呢?誰會把學術當政治鬥爭呢?誰在“叫囂”?與討論新清史有什麼關係呢?姚大力要我們去批評政客,不要“棒打”新清史,我想他應該記得一句老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不能夠在學術上也作些批評嗎?“棒打”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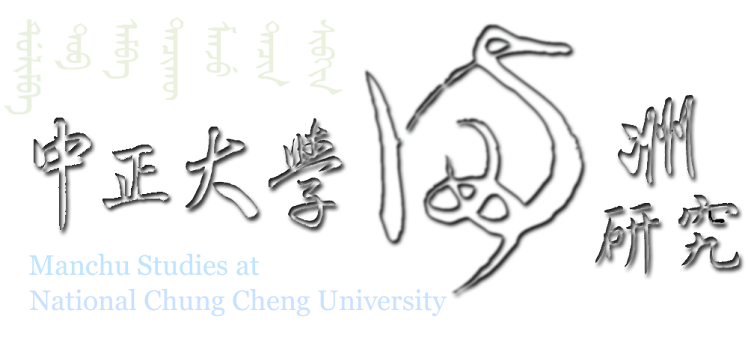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